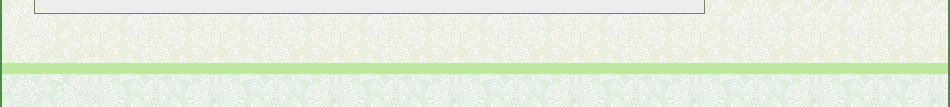在那春耕的日子里
乐一屋
我始终都忘不了50年前上山下乡到闽北山区那些年里难以忘怀的艰苦春耕生活。
1969年2月初,未满18岁的我也许只是出于尽早脱离父母管束的心态,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浪潮涌动下,告别家人,离开榕城,来到偏僻的建瓯县小松公社渔村大队路后生产队插队落户。适逢春耕时节,作为上山下乡知青,自然就立即投身到热火朝天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春耕农忙之中。
在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形势下,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和公社党委在部署当年工作时,都离不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的豪言壮语。因此,我们建瓯也不例外,全县各公社、各大队之间都陆陆续续地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大会,表决心,比干劲。渔村大队广播每天晚上都要公布各生产小队汇报的翻土、溶田、播种、插秧等春耕进度,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我们知青也和所在生产队社员们一样,天上的星星还在闪烁,大家就已经起床,劈柴的劈柴,淘米的淘米,手忙脚乱地生火做饭,生产队长急促的出工口哨声从村口催到村尾,我们赶紧胡乱地扒几口夹生饭,就纷纷扛起锄头、耙子等农具紧随社员们前往队长指定的地方,扎起裤腿,踩进冰凉的梯田,学着老农,一锄一耙,开始用力翻土、耙田、筑埂、劈塝。那几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如《知青之歌》所唱的“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春耕、夏耘、秋收、冬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这就是当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写照。
如今,虽然我已回到城里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了,但是每当夜里我躺在舒适床铺上翻来复去难以入眠的时候,总是常常回想起那些年紧张辛苦的春耕生产日子。那时我每天从田里拖着疲惫饥饿的的身躯扛着农具摸黑回到知青院子后,多么渴望能像村里的农民那样马上就有热饭热菜。但是,收工回来,跨进大门,看到的依旧还是正厅中央的那张破旧案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柴刀、竹篓等一些杂物。几只受到“苛待”的小鸡正围在八仙桌下面,为争食地上的谷壳饭粒激烈决斗。大厅门后角横七竖八地倚躺着几把“重伤才下火线”的缺口劈塝刀和断柄的阔锄头。东屋门框上贴着自创对联: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屋内几张床铺一字儿排开,紧挨门边的那张床铺可谓窝囊,棉被半卷半掀着,枕巾脏得好像炸粿师傅的围身裙,黑油油的。中间那张看上去倒挺顺眼,被子叠得还算整齐,只是床底下浸泡着一大盆换下来还没空洗的带泥衣裤。打在窗口的那张床铺,记得是一位颇会生活的知青哦,半新半旧的蚊帐在窗外阳光的衬映下,给房间增添了些许光辉,一把老式苏州二胡钩挂在帐顶的竹竿上。一张自制简陋的写字桌,安放在房间正中,桌面上除了几本常见的《老三篇》单行本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唱腔选段,还有南平地区以及建瓯县革委会知青办刚刚发下来的《广阔天地》等学习材料。几本《社员记工手册》和涂得乱七八糟的知青伙食团收支流水账,分别挂在桌子左右两侧,桌子旁边的边的柱子上还悬吊着一盏大桅灯,玻璃灯罩熏得黑乎乎,虽然我们很累都不想劈柴淘米,但还是要强打精神抓紧烧水做饭,因为生产队政治夜校的口哨声很快就要吹响,知青干农活差点不要紧,政治学习可就迟到不得!……
窗外一声春雷,惊醒了我的插队生活往事回忆。10年的务农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苦知青生活给我留下许多认识社会的经验和启示。招工返回城市后,每当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顺心、不开心时,我就会以艰苦的酸甜苦辣插队生活做比较,一时的困难和烦恼就觉得没什么过不去,应当、而且可以克服。现在我很珍惜退休生活,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