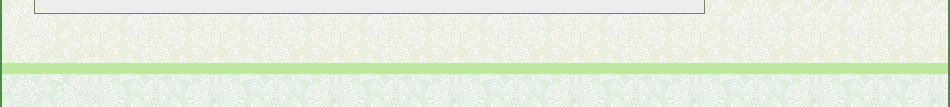我为林场蹂茶电动化跑腿出力
乐一屋
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斗转星移,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地替代、更新原始农耕工具凸显的落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学大寨也借助机械化。记得1975年,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曾经提出响亮的口号,“要在1980年前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在这形势下,全国农村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积极向机械化挺进,各个农忙时节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先后发挥了作用。我上山下乡插队的建瓯渔村大队林场也紧跟时代步伐,也要使用电动蹂茶机。
1975年元旦过后,渔村大队又将我从畜牧场调到由原耕山队扩建的林场。听说是上任的林场场长杨财淼向大队建议,把我再调回林场,日常既耕山劳动也兼出纳和采购工作,协助他做好林场政治夜校读报和管理林场进出现金账款。我没啥理由可推辞,挑着装有棉被草席蚊帐衣裤等物品的箩筐,重返耕山队。
那时,全国农村都贯彻以粮为纲方针,渔村林场从实际出发,靠山吃山,发展果林。我们以种茶为主业,兼种其他山林经济作物,努力为渔村大队的集体经济创造积累资金。林场所属的山地都套种了许多柑橘、油茶、鸭梨、水蜜桃,还有山苍籽。我们的茶园只种乌龙茶,雅称闽北水仙。林场房屋就坐落在满山都是茶树的“老虎垅”山脚,走过一块叫做“水居洋”的大丘水田,与之正相对的还有“前山岗”茶山,遥相对望的两座大山,种着大队林场的几十亩茶树,足足有二、三千株的乌龙茶。林场每年都在5月、8月、10月有一个星期左右的采摘制作春茶、夏茶和秋茶的繁忙季节。有经验的茶农都说春茶生产不但数量多,制作出的茶叶质量也相对较好,每年都能卖个好价钱。春茶采制时间比较长,大概10-12天左右。夏茶季节最短,必须在4-5天内完成。老茶农常说新长成的茶叶“一天宝,二天好,三天就是草”,特指夏茶采制时间很短,夏茶开始头两天采摘下来算是茶叶,三、四天后采下来就如小树叶般厚粗,不值得费工制茶了。秋茶采制也就七、八天结束。所以,每逢采茶制茶季节,我们林场(耕山队)都是总动员,全力以赴,男女老少都上阵,要赶在本季节新长出的那三、四片嫩茶叶还没变老之前,尽快采摘下来,手工制做成半成品原茶,交售公社农副产品收购站,再由他们转售建瓯茶叶厂精加工。我们每一次做茶的目标都是力争制作特级或一级的毛茶,卖个好价钱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采茶跟时令,做茶更要赶时辰。每季茶叶长成时节,采茶妇女们每天采回几百上千斤的茶青,必须赶在当天完成晒青、晾青、揺青、炒青、蹂捻和烘焙等一道道复杂的制茶工序,才能最后做成茶。晒青、晾青、揺青这前几道技术活,我都有跟老茶农学过,虽然懂得了技术要领,但没有单独一项项去完成,很难掌握茶青在萎凋过程中不被破坏,那是全凭经验老道的茶农眼看手摸观察萎凋的情况,适时转换下道工序。炒茶工具是在垒着土灶上的并排三口大锅,按顺序,第一锅先将约2斤左右的茶青不停地翻炒十来下,就抓紧把茶青搬给紧挨边上的第二锅,第二锅又赶紧翻炒几下立即传到第三锅。三口锅分别站着三个炒茶工。我不怕烫手,很愿意炒茶青,别人都是左右手拿着小木片不停地翻炒茶青,我可以徒手不停地翻炒。热心的老茶农手把手教我,如果觉得烫手,赶紧将双手在头发上捋几下接着炒,这样一双手掌就不容易被过火的茶青烫起泡。可是,这不怎费力的炒青活基本上都让给年青女孩做了。林场的男劳力一般被安排在蹂茶岗位。林场蹂茶就是在靠墙根地方,贴地挖坑安放四口大铁锅,离地高约1米的墙壁上横绑着一根直径约莫8-9公分粗的长毛竹,四个蹂茶工面向墙壁双手俯撑着竹竿,挪腰翘臀、小腿发力,一双脚掌上下左右反复不停地使劲蹂捻从炒青锅里送来的热烫烫的茶青,直至每片茶叶卷成索状、全部蹂成一团才算完成,送去烘焙。八个炭火焙笼整夜烘焙不停,直至清晨才能完工。双脚蹂茶是最累苦力活,一双脚掌要经得起热烫的考验,它不但技术要求高,更要展现脚力功夫。所以,每逢开始做茶时,男人们都不想被安排去蹂茶,那是通宵达旦一锅接着一锅不停地蹂捻,没得替换。蹂出的茶汁又会把脚掌浸染得紫乎乎的,特别是下水田后更是连续几个礼拜都洗不掉。为了自我调节繁重辛苦的劳作,同时也打发单调枯燥的的夜晚,年轻的蹂茶小伙子一边蹂茶一边放声歌唱,释放情怀。我和同批下来插队的福州朱姓郭姓知青在蹂茶时常常无师自通地当起了“音乐老师”,把刚刚学来的那时代流传歌曲教给年轻人学唱。新歌本《战地新歌》中《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北京颂歌》以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悦耳动听的歌声飘荡在山间的制茶坊里,吸引着炒茶姑娘们,她们都自愿过来要和小伙子换工,参加蹂茶。那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不过,精神上短暂愉悦依旧替代不了繁重的蹂茶劳动。
听说我们小松公社有的大队林场已经开始用上电动蹂茶机了,因此,大家都希望也有电动蹂茶机代替人工蹂捻这硬活儿。不久,杨场长带我们会识字的几个年轻人专程到兄弟大队林场现场观摩电动蹂茶机,略知蹂茶机是利用曲柄连杆带动蹂桶在蹂盘上作平面圆周运动。炒青后一簸箕茶叶装入蹂桶内,蹂桶在蹂盘内作水平回转,完成蹂捻过程。那时候,一台蹂茶机要700多元,2台同时启用,只需1人操作,便可以省下五、六个劳力。大家都知道那时700多元是个不小的款项,更何况同时买2台,需要1500多元才能买的回来,彻底解决人工蹂茶之劳累,所以不敢抱有过多的期盼。
但是,杨财淼场长管理上有长远眼光,1975年12月,杨场长很魄力地作出决定,从林场有限的生产资金里挤出一千伍佰多元,马上进城购买2台电动蹂茶机回来,尽早解脱大家繁重的劳作。了解蹂揉茶机是崇安县(后撤县建市改称武夷山市)农械厂制造的,那阵子挺有销路,说办就办,去晚了,担心没有现货。杨财淼场长大概觉得我是大城市下来的知青,见过场面,懂得交流,外出办事、待人接物肯定会比本地社员来得灵活些。于是,当年12月下旬末,他派我前往崇安购买,嘱咐我尽快下山赶赴农械厂。可是第二天早上没赶上班车,我只好找机会,上午先做林场木材检尺工作,量好一车杉木后跟着这辆木头车去了建瓯城,接着我马上从建瓯县城乘坐长途客车到100多公里外的崇安县农械厂,来到业务科拿出信汇转账存根联凭证,抓紧签下购买合同,办好发货和托运手续,就在县城找了旅馆住下。上世纪70年代,崇安只是闽北小县城,我已是乡巴佬。那天晚上,我在旅馆吃过晚饭就独自一人去逛街,崇安县城关的中心街市只有不足一公里的十字马路,半小时东西南北走透透,百般无聊,打道回府,旅馆睡觉,次日还要赶紧返回建瓯小松渔村林场。70年代的我居然不懂得利用公出机会顺便游览名胜,更何况武夷山风景区距离崇安城关才4-5公里的路程。当然,那时没有时尚旅游风气,更不会公款游玩。时至今日我还没去过武夷山景区游览,近在咫尺的玉女峰、鹰嘴岩、天游峰、虎啸岩、九曲溪、水帘洞等等著名景点,竟然失之交臂,真是捶胸遗憾啦!
次日清晨我就离开崇安,中午我回到了大队林场,下午照常出工。不久,该厂很守约地按照合同将2台崭新的电动蹂茶机专车长途运送到渔村大队部。接到大队通信员广播通知,杨场长马上派了连我在内的8个全劳力下山搬运。先是2部板车在公路边装车绑紧蹂茶机,每4人负责一台,拉的拉,推的推,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艰难地推向老虎垅山。走完板车路,还要靠人抬肩扛,蚂蚁搬家似七手八脚才把2台庞然大物给弄到林场,暂时撂在炒茶的灶边空地。遗憾的是,因为当时渔村大队电力不足,迟迟没能安装使用。1977年秋天,我调去担任民办教师,较少关注买回的蹂茶机是否已经发挥作用。1979年元旦,我离开插队10年的建瓯渔村,调到厦门工作后更没去过问此事。
2011年夏天,单位派差我到建瓯开会,顺便又返回小松渔村寻找林场岁月的难忘记忆。那天下午到了渔村大队部(村委会)所在地,我就迫不及待地到8里外的前岚杨财淼家里,询问蹂茶机后来的情况。那时80多岁的老杨看到我大老远来看望他,显得格外激动。他记忆犹新地对我说起林场后来的情况变化。他说渔村大队1979年初在前岚自然村新建起一座大功率水电站,80年代初期,前岚电站建成后保证了全大队14个自然村的生活、生产用电。渔村林场的2台蹂茶机就在那时开始发挥了机械化作用。随着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改革,渔村大队林场也改制了,所属的山林作价卖给个人承包,不复存在。老杨离开林场后,那2台象征渔村林场迈向机械化的蹂茶机也不知被被弄到哪里。谈起林场由盛转衰这事,杨场长嗟叹不已,至今还念念不忘当年渔村林场那些年忙碌采茶、做茶、卖茶的兴旺情景。